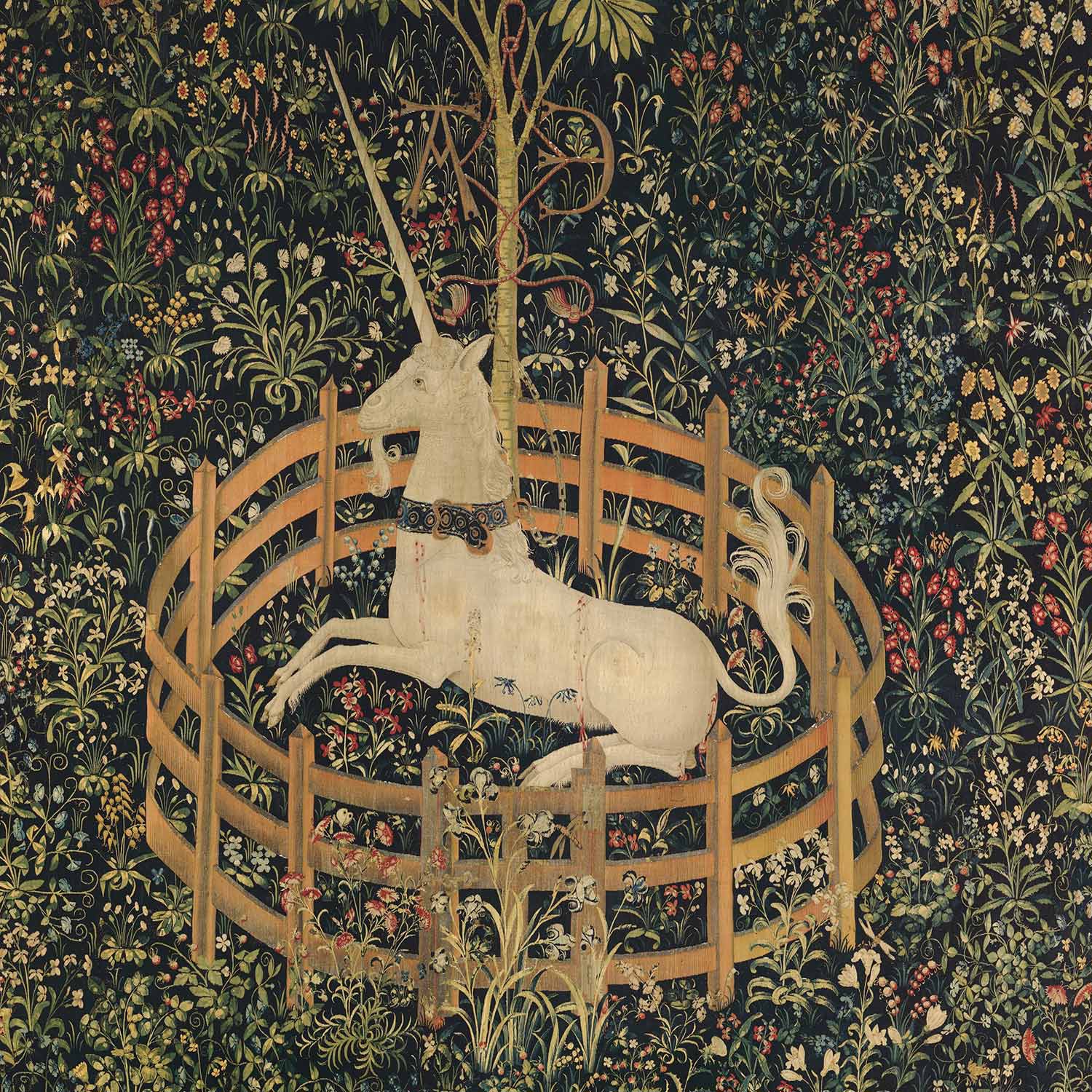type
Post
status
Published
date
Feb 12, 2026
slug
summary
tags
文字
category
长篇小说
icon
password
一
六月,清晨,早读前的十五分钟,蝉鸣比鸟啼还要来得壮烈,这是得势者的嘴脸。它们正巧知道鸟雀不爱吃蝉,于是便叫着唤着,昭告天下他们的存在。它们也被自己的行为限制住了命运,秋风一吹,便要从那树上落下。
今天不急着到班里,我却早早到了学校,往更远的楼梯绕去。手头上还有非做不可的事情。四下无人,进入走廊尽头转角处的课室,从书包里拿出的黑色的塑料袋在我手里颠了两颠,那是幼小生命的重量。我像把夭折的婴儿送进焚化炉的母亲一样虔诚,体会着渐渐消薄的重量将尸体送进课室中间的抽屉里。
洗了手,还在手上抹了些花露水掩盖残留的苦涩气味,回到课室发现已经有人在了。于是把功课放在课代表桌上就趴下,假装睡得昏沉。静静等待着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
我手上的气味不重,尸体也是用好几层塑料袋抽了真空装着,因而书包上也没有沾染怪异的气味。课室里拖动椅子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把我的皮肉展成薄薄一片,心脏与湿润的空气间只隔了薄薄一片肉身——一种神经性的敏感若隐若现。课代表不顾同学的谄媚清点起昨天的作业,值日生也不留情地拖拽着湿透的拖把,路过的鞋子,侧挂的书包都染上了灰色的水渍。在每个人都做着正经事的情况下我也只好坐起来,似是而非地翻书,看不进去的,怎么会看得进去呢?眼睛从左往右,从上往下将书本扫过一遍就翻页。罪恶感早就破土而出,在恐惧的枝叶下消化着,汲取着,现在结出了刺激感的果实,在我眼前闪耀着。
大约七点十五,走廊尽头的六班级传来瘆人的尖叫,盖过了蝉鸣。全部人望出去,看见数学老师张新满脸厌恶地提着一袋黑漆漆的玩意快步下楼。班里的人呆坐在原地,他们的心却跟着张新走了下楼,一丝怀疑的烛光在他们的心里映出了扭曲的影子。
事情很快就从走廊的那头传到走廊的这头:
“碧霞?哪个碧霞?”
“六班那个呀!”
“她柜子里有个猫咪的尸体?”
“叫得吓死个人了,张新听到了赶紧跑过来拎走。”
“她好像很喜欢猫吧,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怎么这件事就发生在她身上呢,你跟她熟吗,带我过去慰问一下嘛。”
“不要不要,张新让她回家放假了,千万不要跟老师的孩子混得太熟,不然什么事情都会找上你。雪儿呀,对啦,今天中午你请我吃饭吧。”
“不行,我生活费也快用完了,谁让你老是吃外面的东西。”
“你家里人这么有钱也会没生活费!”
“那是他们的钱呀,跟我有啥关系。算了算了,就这最后一顿吧。”一胖一瘦的两个女生不知为何总是能玩在一起。二人手挽着手弹着跳着地随着人群流了下去。
学校的监控要在下个学年才能装上,种种原因,这件事大概会被当作是意外吧。
这一天中,每次下课我都会跟着人流佯装去洗手间,在经过她班级门口时借意盯着她的空位。我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但就是忍不住。我想多看一些,用空缺来换取想象的空间,这能暂时缓解我对她的思念。事实也正是如此,我那汹涌的思念从那个空洞泄了出去。失去了实体的她在我的想象中推演着,按照我的喜好,读着我写的诗。
诗歌如何能表达对你的爱欲之火
冬月的北风吹散了牧羊人的嚎叫
一只孤独的羔羊逆着风寻找宁静
脚步渐行渐远,风声愈来愈烈
它呼唤着,我呼唤着,渴求你在我身边
用缠绵轻柔的发丝撩动心中嫩蕊
我愿扒去身上所有的皮毛作回报
纵使畸形似我也要为你烧毁一切
我恨我是如此贫瘠,染上了焦虑的文字
你是我与世界间最大的荒诞
我能写尽生死轮回四季更迭
在你面前却只能怯怯惊寂
痛快像瀑布书写!欢愉像荒草跃动!
都不及你我的灵魂靠近半分
这首像是现代诗的玩意是我送给自己16岁的生日礼物。没错,对生日的纪念仅仅于此。英语课上,老师对surprise、exciting、frightened词义上的解释等价于对“意料之外”四个字的副产品,它们不过是将“happiness”“promising”“insecurity”附加在“意料之外”之上。也就是,开心的意料之外(而非意料之外地开心)。本质上,我是讨厌意外的,因此对于生日派对心里一点期待的情感都没有。生日与过去就是连体婴一样,被迫思考我是如何被推到沟渠里的。实际上,我从来都不在意。这不是对因果的“精神胜利”,我的确不在意自己所处的境地。这世上活下去所需的一切在我出生时就已经全部给我了,那我只要活着,不论什么样的形式便是合理的不对吗?无疑,对,这是我身上那暴力般的诗意赋予我的良善。碧霞看出我身上最大的良善,那便是早早地认识到“爱是永恒的斗争”。
诗会定期组织匿名诗歌的互读会,我们会在下午最后一节课放学后找间空课室围坐在一起评价匿名箱子内的诗。当各位还在说着我的诗歌“拙劣的存在主义亵渎者,连所谓的存在二字都没有弄明白,比起怎么写好一首诗,不如还是先弄清楚生活是什么意思吧,现代诗最重要的还是现实主义的解构。这首诗的作者今天在这里吧,希望你不要嫌我说话直,毕竟我是会长,我坐在这里就要为大家负责的。同样作为一个读者,我不认为读者有义务去揣测诗人的灵魂。就一首诗来说,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诗是诗人借用现实的意象与世界对话。我一向鄙夷用古典的视角来理解现代诗,这是路径上的错误。经典、流行,意味着我们已经提前消费过它,建立在这种语境下的诗不过是一块按需烧制的砖头,看到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碧霞就已经体会到我的思想。
“我觉得海辉说得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按照我的理解来改,应该会是这样:
深院舞,乱枝条,无边黑夜窣萧萧
碧眸如玉,乌发如霞,伊人舞自影
离人泪,凄别情,病消瘦,谁人解
双臂尽失,蛛网攀笔,宣纸霜自凝
伊人倚,文笔挥,往昔光景烟渺渺
你觉得怎么样呢?”碧霞在我旁边说着。我俩沿着放学的河道,地上还有雨后的积水,钓鱼的人立在水里等待着。
“你写得的确有韵味得多。”我低着头品味回刚才的对撞,没有多说什么。
“那也是你珠玉在前。我没本事写出这么好的结构。改诗,仿写,对我来说还是简单太多了。一想到要自己动笔,我就开始心慌。这世间最苦的事情就是表达自我。”
“表达自我啊……你也可以试着写一下,逼自己走出第一步。”
“我试过!但完全没有表达的趣味在,只是很痛苦地在挤些什么出来。写诗是有门槛的,不是技巧上的门槛,是要灵魂复杂到一定程度才有需要表达的东西,这修炼不了。一看到自己那扁平的灵魂就讨厌。”
灵魂的复杂性,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指标?碧霞也没有跟我解释,巧妙地绕过了这个话题。这一个概念,只能从结果倒推,不能从起点的灵魂出发。诗歌,应该是一个人自我表达的途径,为什么要假设一个读者在我们面前呢?为了那不存在的人而左右自己的表达,写诗的意义不就消解了?诗歌是诗人用现实的意象跟世界的对话。这句话我很认可,海辉却默认诗歌要被别人读懂才能对话。这太荒谬了,跟世界的对话从来不是寻找世界的真实,而是找到“我”的真实。灵魂的复杂度就在此,诗是轮船,诗意是舵手,而晕船的人是无法驾驭诗歌的。碧霞大概是被诗意蒙蔽了双眼,受到海辉错误的指引,才将诗意当作是灵魂的指标。我选择了诗作为我的喇叭,那么读者若要读懂一首诗,就得让他好好看看我的灵魂不是吗?我的灵魂是我的,要让谁进入、读懂,是我的选择,我不会屈服。碧霞读懂了我的诗歌,也就意味着她明瞭我的灵魂,是我的灵魂选择了她。我们将会是彼此最虔诚的牧羊人。可惜她的灵魂还没有我的空间,我们之间还差最后的一个壁垒。我必须选择一些其它的方式,来跟世界对话,诗歌这种机械性的语句还是太寡淡了……诗意……我身上这暴力的诗意……
如果旁人看到我与碧霞,必定会想到这种看着普普通通不修边幅的男孩子怎会跟那个女孩子走在一起。各位,请好好品味一下,我是被冠以“这种”来指代的,而她,则是“那个”是特定的某人。真正张扬有个性的人在这个时代都是庸俗的,个性的强韧正经历着一种削弱。离群索居变得普遍,人人都想在自己的脚下画一个圈,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朋友以及朋友的一切都囊括进去。他们可悲的安全感就只有这么点了。而我却不是,我稍弱于个性,这却让我有了一定的独特性。人人拿第一,那么第二就显得稀奇,当然啦,第二永远不会被人记得。我既不在别人的圆圈里面,也不执著于占领一个领土,这不是生活哲学,这是生存哲学。它也没办法进一步发展成生活,这就是我的生命的顶点,也是我的局限性,我只能这么活着。
我们穿过公园,大门的右侧有一座道观,廊檐垂直着一字排开,其门口正对着湖,散发着一种温柔而又矜持的气氛。内里有很多动物,碧霞会学着里面的小道长亲昵地称它们小师兄。猫跟狗就就凑了过去,用鼻子试探着她的气味。我讨了口水在一旁坐着等她,她时不时会将动物往我身上引。我有些害怕动物软绵绵的手感,碧霞却不停喊我把手放在上面,好像乐趣在我不在它们身上。伸出指尖在橘色的猫脑袋上蹭了一下逗起了它的兴致,跃到我的怀里蜷成一团棉花,毛茸茸的轮廓闪着太阳的金光。看到我愕然的反应大家都笑了起来,碧霞帮我把猫从身上抱下来,离开了公园。我跟碧霞一路分享自己那几乎单纯得天真的见解,走到工字形人行天桥上,缓缓穿过被车辆扬起的尘埃。忽然觉得她与这个人工的、几何的、冷漠的世界格格不入。顺着马路的两个方向各有另外的天桥,如果我们是站在另一座桥上,又会说些什么?
我想,时间再过几十年,我都会回想起和她在一起说的每一句话。跟她在一起的傍晚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因果,我唯一的使命就是去碰见她。我悲观地觉得我再也碰不到像这样能够理解我的人,可同时,我又感到幸福,能在懵懂的青春期找到人生所有课题的答案,这是她赐予的使命。再过三十米一到桥的那头,我们就要分开。这三十米像是永远走不完一样,我的文字只能如同西西弗斯般经历永恒的苦行,如果没有她在前方,我大概是很乐意走在这无穷的路上,就跟加缪所说的那样: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西蒙娜在加缪心里从来没有占据过最重要的地位才能轻而易举地说出这种话吧,若是有那么一分一秒加缪能想起西蒙娜,还会这么轻飘飘地断言幸福吗?
当天晚上,我回去那个道观,门前柏树把月色压了回去,走过的时候心里有种抑压感,跟初中体育课上要测一千米时的感觉差不多,那是拼命让自己激动起来的欲望跟恐惧感缱绻在一起一样的体会。大家还没睡,公园没有树的地方能看到她的家,灯还没暗,我正坐在没有靠背的石凳上看着楼上发呆。十分钟过去了,那间房子暗了下来,扳动了水闸把冷漠放了出来,整座城市的氧气被它抬起几分,胸腔不愉悦地起伏着。令人不悦的冷漠为猫提供的恰到好处的养分,夜幕一落下地上便会长出茂密的猫。我像农人一样往道观门口撒了一些肉干,等着它们从地里长出来。不一会儿,一只黄色的猫精神地踏着步出来,试探性地舔了肉干。我站起身本想草草将这件事办定,又被下午与它的亲昵推了回去。不一会儿,后面跟着一只俗称“乌云踏雪”的猫,四只白袜拖着慵懒的步伐朝着黄猫走去。两只猫相互蹭了脸颊,然后脸贴脸尝起了香肠。它俩的缠绵像是在对我挑衅,那几只毛茸茸的脚要把我揉进这惊恐的夜里,我愤怒地站起来,用黑色的塑料袋把黑色的猫套进去,迅速躲到河道旁的栏杆下,掏出外套里的羊角锤挥了下去。
睡梦中作恶,或者说,人们在作恶时睡觉。这些麻木而冷漠的睡梦者把世界拱手相让于我们。粗线条与我们的形象不符,我们更像是这社会上的细节,不能指望良善真的看到我们,而就算看到了,他们也只不过抱着猎奇的心理,高高在上地批判一番。要真阻止我们,他们又嫌隙起自己来了,口口声声“我和你不同”,然而,他们被动的良善却让出了一条康庄大道给我们。他们唯一做的,不过是背对着我们与盟友在言语上谴责我们罢了。
中午的时候,班主任余凝听说我是最早到学校的,把我叫了过去问话。靠近门口桌子上堆着比人高的作业,余凝的背影正好对着我,我敲了敲门没有发出其它声响,只是看着办公室另一边的窗口,外面有一些小人在打着篮球。
“这里有个三明治,不用客气,拿来吃吧。”余凝侧过身子递来一个三明治,办公室里只有余凝一个人,面对操场的窗户能闻到张新位置上淡淡的烟味。
“不用了,我不饿。”
“拿着吧,下午有我的课,万一你饿了可以吃,我不批评。”她把三明治放进我的外套口袋,“今天原本打算去饭堂吗?”
我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
“饭堂就那么恐怖吗,找个朋友吃饭也不乐意?这两个月你都没有去饭堂吃饭啊。”
“我只是不想跑,就坐在课室里做作业,忙起来就什么都忘了。我这么大人了饿了自己会找吃的。”
余凝长叹一口气,看起来无奈地用笔敲了敲桌子,“老师不是你的敌人。不过,身体是你自己的,要是你不想也没办法。今天你是最早来到学校的?”
“嗯,是的,醒得早就早点来。”
“吃早饭了吗?”
“还有昨晚留下的一点面条我热来吃了。”
“行……”她把椅子拉近一些,严肃地问,“早上那件事你知道了吧,你来学校的时候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没有……”我佯装思考的样子,试图将眼前不断闪现的猫驱散。“我回来就趴在桌子上了,没有走去那边。”
“碧霞说那只猫是平日放学经常逗弄的那只,我们再三确认过她的确不像是记错的样子。”余凝一直盯着我,沉默压着我的耳膜,像落入深海一样若隐若现听到远处的噪音,直到眼前是红红一片,跟昨晚那颈部流出来的血一样闪着光。
“是那只猫啊……”,我的食指跟拇指相互在外套的口袋里摩擦着,余凝轻轻拍了拍我的手。“既然不知道那就没事了,你也不要太害怕。”
你也不要太害怕。是我多心了吗?害怕后面似乎应该还有后半句话。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似乎都是善意的提醒,可我总觉得在转角处藏着的影子是另一种威胁,悄悄地从门缝摄进一张拼贴出来的威胁信,“我知道你干了什么”。
课室外,海辉正跟雪儿聊得欢快。海辉看起来很轻松,没有面对心上人那般的患得患失、小心翼翼,能恰到好处地释放自己的幽默感。他几乎对所有女生都是这样,绅士的谈吐,八卦新闻的调侃,不涉及任何个人生活的试探,巧妙地周旋在其中。他与其它女生的丝丝情愫跟菌丝一样隐秘而繁复,好像他就是用女生的好感凝练出来的生物。不过想到他是单亲家庭,他的母亲一个人将他和姐姐带大,如今他跟其他男孩不一般的状态也就有因可究。班里五十人只有他一位是非独生子女,母亲也只有姊妹没有兄弟。在普通的男孩子眼里他是被女人带大的,不过他们对他呈现出来的是畏惧、嫉妒,仿佛他们被海辉一个人包围,独生子女们的独立没有促成他们的勇气。
海辉看到我出来,立马就跟雪儿道别,朝我使了个眼色。戴上他那圆框眼镜朝我跑了过来。故作神秘地对我说:“是你做的吧?”
“什么意思?”我问。“什么什么是我做的。”
他朝着楼梯间往雪儿的反方向走,我不知道为什么跟随他并排走在一起。“就是那只猫的事。”
“我也被吓到了。所以不是我干的。”
“这里不是法庭,真相在我这里没有意义。不过,我也不是真的有什么确切的证据。我只是觉得你是最可能做这件事的。”我们走在楼梯间,回声一层一层从四周叠在我的耳朵上。“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诗会上所有的批评都是面对你的。”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笑了出来,“我不是针对你,好吧,或许有一些,但不是恶意的针对。而是我觉得这些诗歌就该是你写出来的,并且只有这些诗歌才有被批评的价值。简单而言,你身上有一种没办法掩盖的才华,你能写的东西跟你人的气质是相符的。所以我会觉得你像是会把那只猫放在抽屉里的人。暴力跟诗意,永远是并列在一起的。”
你能从他的言语中感受到的不是恶意,是一种强烈的安全感,没有丝毫攻击性的猜忌,像是长兄在河边许下的诺言:哈!我就知道,我不会跟别人说。哪怕没有诗会这个借口,我想他也能笼络一批忠信。这种安全感的来源来自于他对诗意的执着。在他心里,他对诗歌有自己的理解,因此他并不是希望站在道德的角度评判我,只是想要就事论事地验证一下他的理论,有关诗意与暴力的理论。
我跟着他走在正午的校园里,身上微微蒸出汗来,一起讨论有关诗的话题。从惠特曼聊到闻一多,从李清照说到雪莱。经此一役,我发现我跟他身上的相同点意外的多。东由多加、柳美里跟寺山修司是我们主要的探讨目标。海辉为这三人设置了一个光谱,衡量三人的情绪化程度。绕不过去的经典便是《寺山修司少女诗集》,诗歌里出现了很多超现实的意象,结合他在《死者田园祭》中的影像表达不难看出他一直在寻找超脱于现实的空间,在这空间里面才能重拾清醒,摒弃羞愧。他是这么说的“人们认为在友情的世界是难以跨界的,那里有着彼此浸染已久的习惯、思维模式、兴趣爱好、甚至流言蜚语。”在决定与谁做朋友的同时,也决定自己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不是吗?说起来有些暧昧的意味在,不过我认为你也在寻找一个超脱于现实的空间,这股冷漠的欲望是一种天赋,而我对于拥有这种天赋的人有一种敏锐的品味。你很危险,你的诗歌里面充满着一种抵抗健康肉体的暴力,你大概是没办法忍受健全的人出现在你身旁,因而你才进入诗会的吧。诗会不光有碧霞,还有诗歌,诗意的表达能暂时性地支撑你那暴力的世界,所以我才会说,你身上的是暴力的诗意。我认为我们会是很好的朋友。最后引用一句:“有着讨厌雨天血统的马,就无法再雨天奔跑。人类也是靠血统来疾奔的。你既然有那样的血,就请继续书写吧。”我相信你的才华会带来一段截然不同的道路。
余凝开教师级会后在背地里说过我有是个有才华的人,出于缘分,在楼下的我刚好听到这段对话。她说在跟我的父母沟通后明瞭我的个性为什么如此沉寂、不爱说话。我的心里却产生了新的疑惑,这里所说的才华是什么?是像加缪那样消化寂寞的能力?还是汪曾祺那般提炼生活趣味的天分?才华,是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名词,它只能概括现象,却不能真正地认识一个人。我不了解才华在余凝跟海辉的眼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是令人嫉妒的宝物,还是避而不及的利刃。
余凝的老公来过学校几次,鼻头上透光的疮一眼就能记住,更容易令人记住的是他身上那阵酒腥气搭配上干净的立领polo衫,小臂还有一道从手腕拉到手肘的疤痕,两个余凝并排站在他身前都不一定能挡得住他。正是这么个凶狠的形象在余凝面前却被管得娇滴滴。余凝是大学是学汉语言文学的,而他老公是干工地的,从蓝色头盔干到红色头盔后就向她求婚。听他们八卦,余凝似乎出过一本书,但市面上的流通量很小,怎么也找不到。如果单独看他们的照片,两人的形象绝不般配,可如果看了他们的互动就瞬间成立了。原来才华,就是俗人画的一个比天大的靶,挂在别人身上,好让自己有理由爱上她。自从她怀孕后,她的眼里多了几分幸福与缠绵,她肚子里怀的,是她的亲生骨肉,可惜她的身体太小,只能把另一些亲生骨肉丢掉。
随着碧霞放了三天假,事情很快就冷淡下来。碧霞回到学校主动提起了那只猫,想主动找回往常的氛围,但她因泪水发涨的脸颊还是让人心生怜惜,对方说起话来仍旧小心翼翼。她缺席了接下来的诗会,等到他爸张新下班一起回家。届时,我便在门口看着她骑上自行车,后座坐着张新,他俩的衣角循着蹬车的节奏拍打空气。独自回家的这些天里我不再绕道去公园,沿着马路一直走。人行道上骑过的电动车每次擦肩而过,他们被我踹倒在地的景象就会闪现。有次我真的动腿了,对方甚至没有看我一眼便扶起车继续在人行道上骑车。我沮丧极了,怎么大家都这么冷漠,碰了壁也不愿更正呢?我不断释放着微小的恶意,故意撞上低着头玩手机的路人,对在商场独自排队的小孩偷偷说你妈妈已经买单走了。有且仅有一次,我被路人训了一通,对方看着有五十岁,带着蓝牙耳机,另一只耳朵却贴着翻盖手机:“屌你老母”。我开心极了,原来还有关注这个世界的人啊,我回头看去,对视了一眼,笑出声来,那绝对是友善的笑容,可他看到我的友善却失了魂,低声骂了一句就快步走开。
我与碧霞之间也有绕不过的尴尬。中午,她没有去吃饭,而是翻着闻一多的《红烛》,她周围生人勿近的气氛把课室擦亮了,谁也不好意思把灰尘踩进去。我的喉咙像是呛入了不合时宜的空气,开不了口。她沉迷在书页没发现我之前,就默默盯着她发呆。发呆是思想通过视神经把幻想聚焦于瞳孔的成像过程,在盛夏的日子里,我所能想象的,是她的发线被烘出香气的过程。这是诗页上的纸墨在她脑中陈化所得的香气。
“很吓人吧。”我终于开口问道。
“唉!”她长叹一口气,“倒胃口!”
“你放假的日子里我也没有去诗会,在那边坐不住。”
“怎么说得像跟我有关一样。其实我要去的话倒是也可以,不过目前我想先把诗歌往后放。”碧霞阖上书说,“我想明白死亡是什么。”
我没有说话,严肃地看着她。
“你别这么严肃!听起来很不好意思。不过那只猫死了之后尸体被我爸丢了,我多少有点愧疚。毕竟是跟我亲昵了一会儿,它的生命我认为是要负上责任的。”
我看了桌上的《红烛》,没有再说什么。她没有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命运,转而去悲悯被死亡的阴霾笼罩的每一个生物。这是天真的博爱。傍晚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潮水褪去露出闪着黑光的滩涂。海浪一次又一次冲刷,把鸥都惊了几分。空旷且潮湿的阴天,占据了她生命极长的一段时间,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意外,没有哀伤,只在她分叉的脚尖留下来自过去的粘腻。正是在这恒久的“无”中,碧霞她踏上浪花,不分四季地在海平面上翻腾,跳跃,没学会静便懂得动,没经历生便思考死,她超出了“我们”二字,从海中汲取一切她所需的东西。
“嘿,嘿,你在想什么呢?”碧霞打断了我对她的探索,“你看着很不对劲。”
“没事,我只是在思考忘了什么东西。”
“忘了的东西也能思考吗?”
“可以的,死了还能把坟刨出来,忘了的东西有什么不能想起来。”
“其实你什么也不会忘记的。”有个声音跟我说,我把它写在日记上。这是我写日记的第一天,也是一切的开始……
- 作者:dororo有几何
- 链接:https://dororodoujo.com/article/305a3021-e025-802d-a6e9-d3f81da015a6
- 声明:本文采用 CC BY-NC-SA 4.0 许可协议,转载请注明出处。




.jpg?table=block&id=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t=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width=1080&cache=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