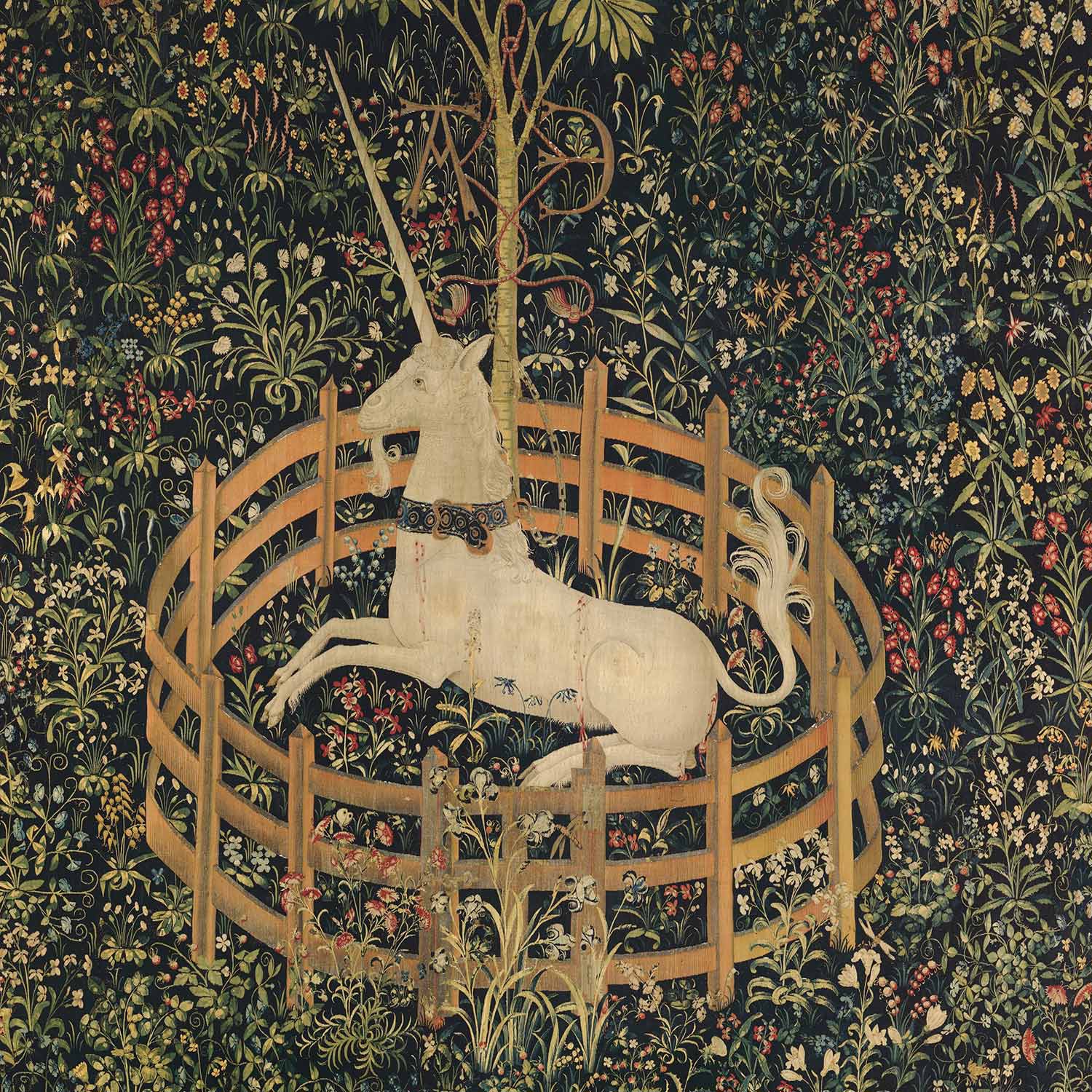type
status
date
slug
summary
tags
category
icon
password
蒙田与外界“不抵抗”理论,或许可以归因为他在政治生活中的挫折,才转向心灵寻求庇护。这种简单的生活避免了真理与死亡的思考,同时也像是真正生活的“仿造品”。轻松地游荡人间,本质上是将私人生活当作是生活的终点,这会导致责任生活的衰弱,同时对现实状况也不再关注。在这种生活中,蒙田没有提过与他人的链接该是如何,或许陪伴他的人心里也在默默地批判他。蒙田的“人文主义”的内在满足在旁人看来,或许也可以被称作是“非人道的”。
布莱兹·帕斯卡尔以一位科学家的身份一阵见血地表达了对“蒙田主义”的质疑。帕斯卡尔在他年幼时就展现了极高的科学素养,然而,在成为科学家之前他还是虔诚的奥古斯丁派基督徒,这一复杂的身份为他提供了两种看待世界的两种不同视角。
蒙田式内在满足期望重建起自然与人的联系,希望人们能从自己的起点找到人生的答案。放在东方,这就是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但从帕斯卡尔却从科学方面无情地证明了,宇宙并非人类安枕无忧的家园。随着科学自然主义的发展,人类对超越性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而非削弱。这就像是再说,人要想获得安宁,就要避免科学的熏陶,而这显然是错误的。宇航员们亲眼看见完整的地球后再回到地面上,看见人们还在为了政治、观念、工作、权力而拼个你死我活,往往会因疲惫而患上抑郁。我们可以出于人道主义,不再将宇航员送上抑郁的行刑台上,那么科学自然主义则会得到停滞。以上粗糙的论述我们可以证明得到蒙田式的内在满足与科学自然主义存在着一种拮抗关系,矛盾的点在于,蒙田式的梦想在于向内收缩,科学自然主义则是向外探索。
帕斯卡尔是科学家,但他的宗教生活经历又让他不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他旨在洞察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包括思想。他敏锐的察觉到蒙田式生活当中重要的一环——消遣。帕斯卡尔认为靠消遣来自我安慰就是人类最大的痛苦。帕斯卡尔举了狩猎的例子,倘若君王们能直接杀戮动物获得尸体,而剥夺他们狩猎的过程,那么君王们将不再热衷狩猎。人在消遣的动机需要结果,更需要过程,蒙田在与自然交互的过程中也尝试为自己的过程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灵魂渴望休息,但倘若灵魂一直休息它就会渴望活动。至于什么是活动,现代人的躺平是否算是活动?这一问题则在《薄伽梵歌》中的“弃绝者”与“行动者”中有所讨论。但究其而言,灵魂活动的合理性是灵魂自身赋予的。
帕斯卡尔认为,人类对消遣的热爱,不仅鼓励我们参与娱乐活动,也鼓励我们参与进包括政治在内的最为严肃的活动。当他有机会参与王子的教育活动中,他表现了强烈的奉献觉悟。同时他也察觉到自己参与政治生活的内在满足感的实质存在着“分散注意力”。作为政治参与者,每天要接待形形色色不同的人,固然,这种权力与责任并存的职位为参与者们提供了虚荣心。但责任同时也将我们不再只关心自己,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其他人身上。
“我们追求真理,却只在自己身上找到不确定性。我们追求幸福,却只得到了痛苦和死亡。我们没法不去追求真理和幸福,但也没法真的获得真理或幸福”。西西弗斯式的生活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而像加缪那样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人寥寥无几。消遣有助于转移我们对徒劳生活的注意力。但如果我们所悲伤的不仅仅是自己身上的各种事情,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处境,那么分散我们对悲伤的注意力,就相当于分散我们对自己的注意力。
帕斯卡尔主张主动面对着悲惨的生活,热衷于参与严肃的社会活动。帕斯卡尔说到,人们希望“正义”,无论人们对消遣这件事是什么态度。在自我欺骗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利用欲望骗自己,也打开了让别人欺骗自己的大门,政治取向的不同便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革命是构建政治秩序的过程,一切的革命都是基于犯罪,一切的革命都是基于武力,一切的革命都是正义的,一切的革命都是真理的。大家都希望将真理、正义赋予强大的力量,以让其永存,但若是真正的正义与真理,又何须武力作后盾?帕斯卡尔所说“因此,既然我们无法让正义的东西变得强大,我们就让强大的事情变得正义。”正如彼得·克里夫特(Peter·Kreeft)所说:给大炮贴上口号,比让大炮服从口号,要容易许多”。
帕斯卡尔也因此哀嚎:政治所给予的远不及我们在政治的需要。
帕斯卡尔笔下的人类是矛盾的,这跟他的科学与宗教生活有关。在他所写的《赌注》一文中,他认为,用短暂而有限的人生做赌注,来赌一把永生的机会是相当划算的。哪怕上帝有不存在的可能,但哪怕是千万亿万分之一的机会也抹不平正无穷回报。用冷冰冰且功利的方式论述宗教行为的帕斯卡尔似乎已经摒弃了他的信仰,他好像在跟与他同时代的皈依者说:我们应该简单地重复宗教活动要求的各种动作,直到我们能有效地让自己的理性缄默不语。我们在此稍放一下,要想探讨在他心中的矛盾之处,我们得要从他的另一句话入手:唯物主义者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物质,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任何事情。一个始终如一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会和人争辩;他会直接动用武力。事实上他根本不会去思考,因为他不过是物质。
这句话恰好是理清其矛盾处的润滑剂。帕斯卡尔提出了一个悖论:倘若人的答案就在人本身,那么人将超越人,这是不可能的。但同时,人类又有着向上的倾向,人们觉得自己理应生活得更好,苦难让人们意识到,实际情况与应当状况隔着一个鸿沟。人类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人类伟大的可能(自我超越的可能)。
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与书中不同的观点:帕斯卡尔依旧让人机械化地重复宗教活动,并非是要扼杀自己的理性,恰恰相反,人们能从这种机械化的宗教活动中重拾理性。当我们机械化地执行时,上帝恰恰从我们的心灵出去了,剩下的只有理性。那为什么不直接抛弃掉宗教这一事物呢?因为这根本是没有必要的,帕斯卡尔并非想要否定宗教,不然他也不会为了自己的教义辩护,他想将宗教当作是一面镜子,人无法明确自己的信仰,是激情使然。理性把人们带到了宗教的境地,然而心里却无动于衷。那么就请用理性说服自己吧,不需要收集上帝存在的证据,而是削弱人自身的激情。同理,宗教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信仰主体,当我们虔诚而机械地履行各个职务,我们的理性就会愈发膨胀。
理性膨胀的过程不一定是愉悦的,大多数时候伴随着的都是焦虑,但至少在机械式运转的过程中,能有效地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重新呼唤出理性到达不了的境界——心灵的真善美。生活中,我们认同成功,以受苦为耻,因此现代人不断地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美好的生活,也正因如此,我们在离开社交媒体时,转瞬即逝的哀伤就会四面八方地涌来,社交媒体展现地越是强烈,哀伤就会越明显。当我们将自己安排进某种令人满意的范式中,同时也就扼杀了我们哀伤的机会。一旦失去哀伤,否认苦痛,我们便停滞了,失去了自我超越的可能。这种自我超越,并非是焦躁不安的,而是真正重新拥抱自我超越的可能性,信仰背后的超越性存在便不再隔着不可逾越的距离,而是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
- 作者:dororo有几何
- 链接:https://dororodoujo.com/article/2b1a3021-e025-8098-ac54-cf6165866141
- 声明:本文采用 CC BY-NC-SA 4.0 许可协议,转载请注明出处。




.jpg?table=block&id=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t=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width=1080&cache=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