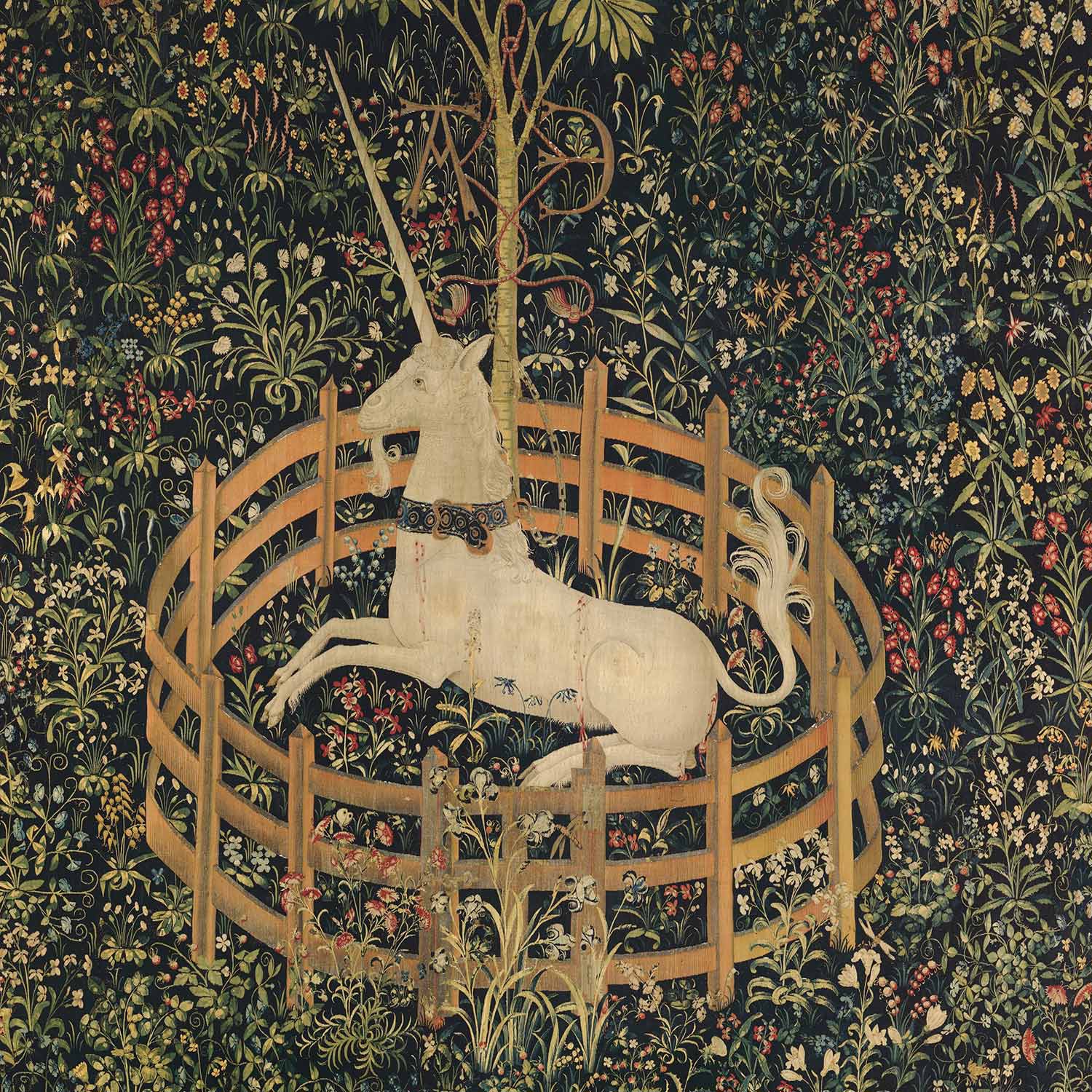type
status
date
slug
summary
tags
category
icon
password
痛,持续的疼痛。在二十五岁的第一个月,针刺感不定时、不定侯、不定位置、不定程度出现在我的右侧后脑勺。恼人。疼痛出现的规律处在一个暧昧的地步,我不能主动复现这个疼痛,却又大概清楚是因何而起。因为无论我怎么动我的脑袋,它都不一定会疼,但它却总在别的地方偷偷捏你一把。譬如打哈欠打到一半时,神经就会抽一下,把舒畅的呼吸中断,令人特别不愉快。
痛一发作起来有种牵扯感将我的头往右拉,一阵一阵,我跟个摇头娃娃一样,跟着它的节拍抽着。这让我畏惧起来了,一是害怕衰老,二是害怕育儿。
衰老总是伴随着疼痛。这句话乍一听没啥问题,但细细想去,年龄、疼痛两者难说有正相关关系。从出生开始,我们便一直经历着疼痛。剪脐带的痛,哭得膈肌痛,笑得腹肌痛,喘口气喘大了喉咙也会痛,总而言之,人生是痛的,不论男女老少,痛苦有平等的机会落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只能说随着人的衰老,对痛苦的耐受程度便下降了,痛苦是客观的,对痛苦的感知却是主观的。
学生时候中午下课,为了早早吃上饭而跑去食堂,顾不得湿滑的地下,不料脚一滑没停住径直撞上钢管。听见后面的人惊恐地“噢”了一声,又把我吓到,我害怕输,简单的一顿饭是我在学校能获得的唯一胜利。我简单拍了下身体又接着跑。直到午休趴在桌上身体才渐渐痛了起来。科学来说,这是人类的捕食本能促进肾上腺素的释放,降低了人类的痛感。不过随着年岁增长,要为了一顿饭赢的心态少了很多,生理上对痛苦的处理能力下降了,对痛苦的感悟也会更深。
好比在刚才的思考过程中,我觉得为了在一顿饭上而赢的我有些懦弱,我的奔跑居然只是为了比别人饱得更早,吃得更好。而不是为了革命、自由、智慧、解放更崇高的目的。读书的时候有进入共青团的渠道,当时我们都不明白团员的身份意味着什么,而老师是对我们这么说的:现在的重点高中看到你是团员都会放宽要求,同一个分数,当知道你是团员就更有机会进去。入团的手续并不繁琐,写个文章就好。当时我便觉得自己身份伟岸了起来,而伟人的身份是伴随着特权的,要获得特权的代价也并未想象中的大。直到凭着自己本事考上市重点,却发现身边清一色都是群众,我便觉得这股劲好像用错地方了,甚至自己的身体也下作了。小时候叔叔在地上丢个十块钱假钞我便跟姐姐在地上争抢,没想到时隔多年我还上了这个当,反倒显得我的人格廉价。晚年的尼采持续受着病痛的折磨,却写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倒好,稍有不舒服却觉得懊恼。怎么就不再严重一些呢?这样我才好有理由休息。我这种人大概是没本事当革命者,也没有被笼络的价值,光是自己就把自己骗倒。
小时候装病也是常有的事情,每个月总有那么一天极其讨厌上学,我便想尽办法装病。装病干嘛?我也忘了,当时哪怕回了家也不能偷打电动,也没有朋友一起,大概是单纯想要一个私人空间缓一口气。六七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在装病这件事上得心应手,直到在校门口听见老师偷偷在说:反正这孩子总是装病。我好似领悟了什么一样,后来的日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大的掌控,能假想一个不存在的危险来欺骗心脏,让它把血液集中起来,从而降低体温。某次,探热针放在腋下十分钟后拿出来还是停在34摄氏度。我也把自己吓了一跳,莫非我真是病了?但我深呼吸,从装病的状态抽离出来,又感到自己的脸上暖了起来。我这才放下心。
下作,对,跟他们比我确实是下作的。海伦·凯勒,卢梭,尼采,梵高。以及想象中应如是的自我。我既不坚韧,也没有能把痛苦巧妙转换成经历的技巧。许多伟人并不忌讳痛苦,把其看作是“益虫”也大有人在,而我的田里没有种子,只有泥沙,生活就这么敞开大门被痛楚慢慢侵蚀。
我并非想论证“痛苦是有价值的”,但作为一个创作者,却不得不想入非非。一个人若是少了创作力,就少了再活一次的机会。若是我年老力衰,或是不幸患上重疾,我最为担忧的是自己的创作少了气力,而我却又不是一个坚韧的人。痛苦磨练不了我的意志,只会消耗我的心气。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加退缩。上面这件事上,或许只有一件事值得庆幸。我身上的青春还未殆尽,痛苦还未完全磨练完我的心气,面对生活我尚有力一战。
第二便说到育儿。孩子刚出生一无所有,直到三岁前都寄生在父母身上,不知疲倦地攫取周遭的经历。东摸摸,西碰碰,不满足了还要放到嘴里咀嚼。这大无畏的气势一到六岁就没有了。届时,他们已学会对家长察言观色,学会试探性地推进自己的触角,父母稍有不悦便怯懦了。
孩子怕痛,但他们大概不畏痛。而孩子的父母反倒不怕痛,而是畏痛。孩子玩砂锅被烫了一次,下一次还要继续试探直到再一次烫伤。这叫怕痛而不畏痛。而父母们在孩子们烫伤后反倒没有那么担心,他们更怕孩子的在苦痛之路上的试探过程。这叫畏痛而不怕痛。怕痛是面对生理体验上的本能,畏痛是对精神体验上的恐惧。人一旦有了恐惧,便不能忠诚地享受生活,得缩在安全区内唯唯诺诺。生儿育女便是将人生从多面向,减为单面向的过程。要想享受生活的人是顾不得孩子的。
现在的人们总说,生活跟生存是不同的,这是多面向生活跟单一面向生活的区别。若把人生比作一棵树,那么生命的延续(生存)便是主干,而生活的意义则是枝叶。一颗若只懂得发展枝干长高的树,会被农人挑来培育,经过大批机械化的种植,最终送进伐木场提供木料。若想要不被砍下,那便要想办法拓宽枝叶,增宽人生的宽度,哪怕有朝一日自己被砍下,那也算是结束了被培育的命运了。
害怕育儿,实际是畏痛。鲁迅曾被当时的人批评“为何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对此,鲁迅是这么说的,“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
人踏上苦痛之路不是自愿的,当中甚至还带有些家长制的意味。害怕育儿,是害怕自己跟孩子成了共轭家长。彼此扼着咽喉,谁都松不了手。有些事情还是在我这儿终结就好了。
我一说这种话,就又回到“下作”这一话题上去了。但我想,这些不着调的文字、观念大概是不会被攻击的。生育率高的时候“你不生有的是人生”,生育率低的时候“反正大家也不生”。大多数伟人,是在生命中的某个面向走到极致了,以致其所承受了全人类的苦痛,玛丽·居里长时间暴露在放射性射线下罹患贫血,成果让无数后人享受。倘若居里夫人倒在黎明前夕,那她的苦痛便得不到理解,历史上的名号最终会被其继任者夺取,她却为别人做了嫁衣。世上研究员们大多是这个使命,他们所承担的苦痛与伟人们并无二致,因而伟大的并非是苦痛,而是人类生命中那熠熠生辉的光,得以在寂寞的生命中默默耕耘的耐心。
而我,不过是既想要伟人的待遇,却又不想承担伟人的代价的一种下贱者。这是我这名尤其下作的群众所想要的生活。
- 作者:dororo有几何
- 链接:https://dororodoujo.com/article/2aea3021-e025-8024-b4f6-ee51204b0138
- 声明:本文采用 CC BY-NC-SA 4.0 许可协议,转载请注明出处。




.jpg?table=block&id=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t=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width=1080&cache=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