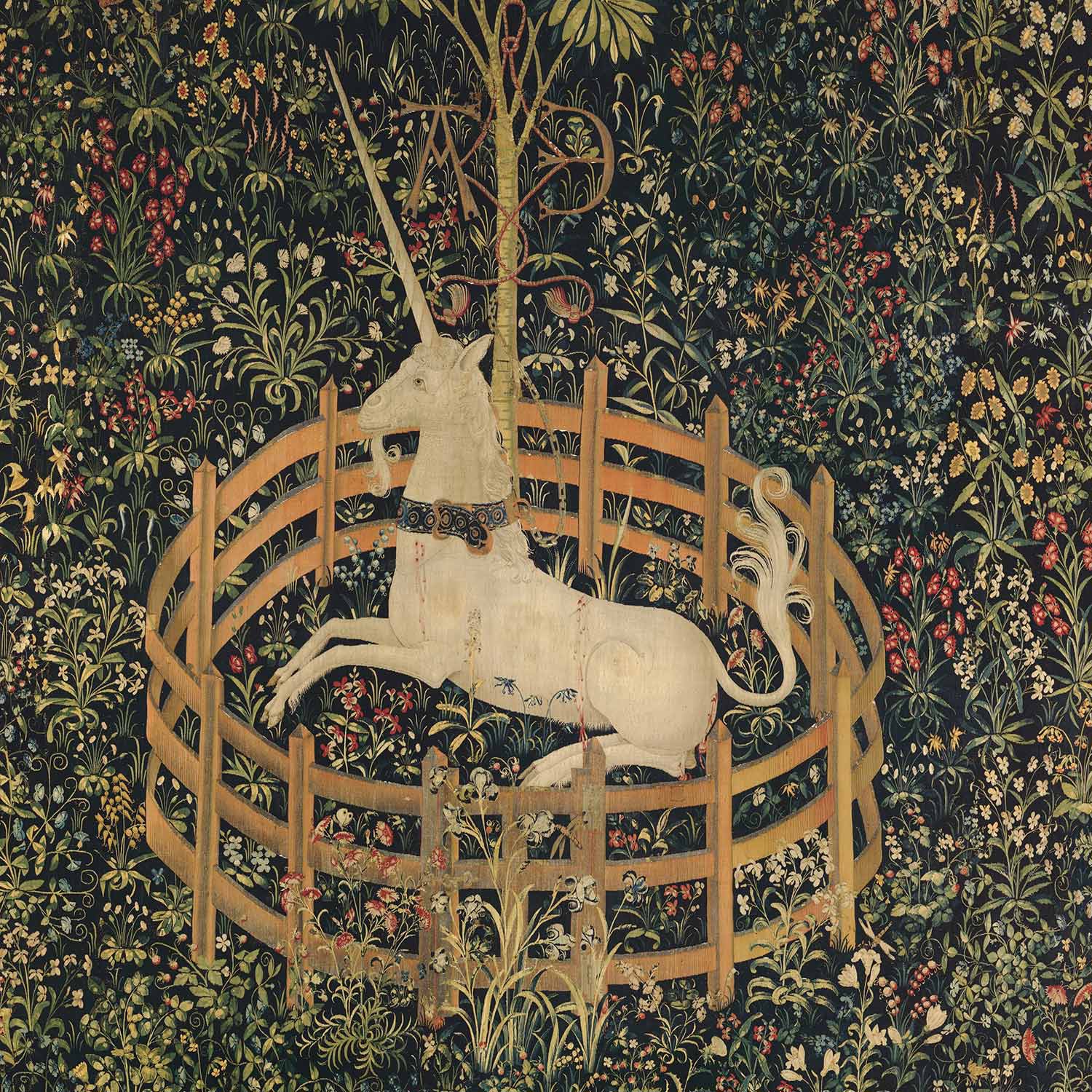type
Post
status
Published
date
Nov 30, 2025
slug
summary
tags
文字
思考
category
学习记录
icon
password
帕斯卡尔的理论中,答案依旧附着在一个“超越性”的存在上,只不过我们并不是靠近它,而是让自己成为它,当中仍存在着一个信仰的中介。人类要通过履行自己的信仰以成就自我。这好像依然否定了人类自身的可塑性,只把人类放在一个永无止境的跑道上,并以之为乐,路的尽头有永生吗?不重要,因为我们在自己的信仰上漫步着,用自己的信念改造这个社会。在这里的论述放在现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陷。在缺少信仰,主张个性的时代中,我们要如何找到自己信念的事物?帕斯卡尔提供的,是无穷无尽的忧伤,他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爱,并认为人们最终的答案是信仰,而这,将导致敌人的出现。哪怕是声名显赫的人,其实私底下也都处境悲惨。在尚未到达终点的过程中(整个人生)每个人之间都是“笑容满面的敌人”。
帕斯卡尔认为我们不幸福,是因为我们与上帝的距离疏远了,卢梭则认为我们不幸福的根源在于我们离自己疏远了。帕斯卡尔认为自然已经堕落,唯有靠上帝救赎,卢梭认为人类已经堕落,得要靠自然救赎。帕斯卡尔与卢梭之间有一个共识:社会生活是丑陋的。无论是谁都无法在社会活动中得到安宁。我们对自身纯粹的爱变得不再令人信服,我们开始需要社会上的评价为自爱作作证,那么,自爱就被扭曲成了“自恋”。我们的自爱仍然存在,但可惜的是,它被外界的华美的辞藻淹没了。我们被这些词汇蒙蔽了双眼,让我们忽略了自爱原本就能带给我们的美好。随着自爱与自恋的分道扬镳越来越远,两者之间的距离令我们不再逾越,这便是“自我厌恶”的起源。我们不断地在社会生活跟私人生活中切换轨道,社会化越重,我们就离自我越远,自我厌恶就会愈发严格。
卢梭思考到如若顺着这条路下去就会归于蒙田那般的消极避世,在孤单与社会生活中永恒无助地流转,自我分裂仍旧无法得到解决。卢梭自信地朝着当时的生活宣战,构想了一个全新的“公民”形象,一个不隶属于教会而隶属于城邦的公民。
卢梭的成果在于,他彻底否定的教会中构造的“人格化”上帝,人们无需以上帝作为自己的道德榜样,而是专注于人类本身。《社会契约论》毫无保留地展示了卢梭对政治赋予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他眼里,政治有着最高的权力,人类中的一切事情(生活,包括灵魂)都与政治有关。良好的政体能让公民的自爱扩散到整个政治体。只要将自己看作是更大成分的一份子。爱国主义理念中,“自恋的力量”可以与“美德”相结合。
这恰巧是柏拉图式的政治转向马基雅维利式政治的转折点。人们以履行自己的信仰为乐,就意味着存在一个途径能够合法,合道德的方式来支配人们的生活——只要道德由政体来构造便可以了。
“好的社会制度,在于最懂得让人去自然化”。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文中他举了一个斯巴达母亲作为例子:在这位母亲看来,只有努力才会哀悼自己为祖国而牺牲的孩子。要在公民的正直中寻到满足,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消灭琐碎的情感。它所要求的是让我们去自然化。
卢梭曾在其它作品中用浪漫的色调描述自然,如今却踊跃地投入到反自然之中。这似乎有些诡异。但我们要认识到,这是卢梭一次酣畅的思想实验,他或许是将自己的思想,也完全投入到探索的过程中。
卢梭在真切地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发现彻底去自然化的生活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这种代价卢梭本人也不愿付出。卢梭因《社会契约论》而被迫逃离法国,躲在瑞士某座湖泊中央的圣彼得岛上隐居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卢梭什么都没做。他在岛上闲庭信步,好奇地鉴赏岛上的植物。倘若累了,他便承小船去另一座小岛,坐在岸边看着海浪拍打水岸。这些轻度的活动令他“从未如此快乐过”。
书中提到这是“单纯存在的美好”,与蒙田那般的生活又撞上了。但相信卢梭自己也清楚,这种所谓的“自得其乐”,是一种谎言。政治的终点是寻找到“美好生活的方式”。这种精致的私人生活真的能从中获得幸福吗?蒙田也好,卢梭也罢,是被社会驱赶至这种地方的,在这之前他们不见得会主动拥抱这种生活方式。因此我很难接受这就是生命的答案。生活是物质的,灵魂是精神的,而社会是复合的,如果我们将美好生活的终点与蒙田生活做匹配,那么人类的社会将骤然坍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被人称赞是令人愉悦的事情,获得友谊是美好的体验,在社会运动中我们同样可以获得幸福的体验。可同样的,社会中的谎言存在着一种令人沮丧的力量。如果我们完全坦诚地表达自己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好友,那么这个世界上将一个好友也没有。我们即希望能完全坦然地面对自己,同时也期望着合群,以获得链接。To be or not to be, 精炼地概括了人道主义的核心疑问:如何在社会中构造起以自我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 作者:dororo有几何
- 链接:https://dororodoujo.com/article/2baa3021-e025-80a2-8ea1-eaf020555925
- 声明:本文采用 CC BY-NC-SA 4.0 许可协议,转载请注明出处。




.jpg?table=block&id=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t=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width=1080&cache=v2)